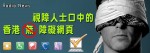【Radio News】1969年3月,那時華富村剛剛建成,我就搬了進來。
最早,不知是一九六幾了,真的不記得。
我大概二十多歲(搬了進來),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。
我看着華富村建成的。
我1967(搬了進來),第一期。
製作:施家勝、歐澧瑩、朱悅瑩、李寶善、張政恒、區嘉俊
【文字版】
華富邨,一個有四十多年歷史的舊社區,當中不少已經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街坊,有的已經兒孫滿堂,在華富邨看著子女如何長大成人,結婚生子;亦有年青時在外漂泊半生,退休後回到華富邨安享晚年的長者。雖然他們的背景、身份都不一樣,但有一點相同的是,他們在這裡居住了四十多年,見證華富邨的歷史,經歷華富邨的變遷,對於華富邨的那份感情難以捨棄。
華富邨位於香港島南區薄扶林,是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公共屋邨。華富邨的一邨於1967年落成,而二邨就於1970年落成。華富邨是當時計劃興建十個廉租屋邨中的第八個,隨著社會發展和交通愈來愈方便,華富一邨和二邨的人口慢慢增加,高峰期共有約50000人居住,但現時只剩下20000多人。根據房委會截止2014年9月30日的資料顯示,華富一邨人口約有12900人,共住了約4800戶;二邨則約有13500人,共住了約4300戶。華富邨見證著香港四十多年的歷史,而見證住華富邨每一個變遷的,就有一班由六零年代開始係華富居住的老街坊。
華富邨剛剛落成的時候,梁伯伯就搬了進來,他憶述當時的設施不多,駛入華富邨的巴士線亦寥寥可數。
【梁伯伯/華富邨住戶】
初初開始不是這樣的,沒有巴士,巴士只是經過村外,沒有進入村內,這裡很荒涼,這裡店舖不多,華安樓那邊只有數間店舖,街市都是很少,初初來的時候。

謝婆婆在華富邨住了四十多年,是第一批住戶。對於華富邨當時的面貌,謝婆婆的印象仍然很深刻。
【謝婆婆/華富邨住戶】
這裡風涼水冷,只是建了華貴邨後,就沒有這麼漂亮,以前的海很漂亮,那時入來買菜,人們拿食物到街口賣,地面四處都是爛泥,沒有街市的,那時買菜要去香港仔,行路下去,那時沒有車,沒有街市,那些人賣魚要在馬路賣,在地攤賣。

謝婆婆認為,華富邨的配套愈來愈好,由她口中所說的爛泥地,慢慢變成一個擁有各樣設施的社區。
【謝婆婆/華富邨住戶】
現在有了街市,有店舖,不用到那麼遠買東西,又有車,幾號車幾號車,多了交通工具可以出去。住在這裡很平靜,治安是最好。{trim} 因為沒有人搶劫,我們搬進來的時後,我們家家戶戶都打開門,小朋友又多,個個都有小朋友,整條街都是小朋友,我們甚至打開門睡覺,沒有無關門的。
這十年變化得最多的,謝婆婆認為是多了新移民,當中不少是南亞裔。雖然語言溝通不到,但謝婆婆仍然覺得和他們相處融洽。
【謝婆婆/華富邨住戶】
沒有什麼特別,他走過看到就打聲招呼,但是溝通就不行了,因為他們的語言我們又不懂,我們說(廣東話)他們又不懂。
同樣在華富邨住了四十多年的毛伯,見證著華富邨的變化。但對於多了新移民做鄰居,他的看法就和謝婆婆不一樣。
【毛伯伯/華富邨住戶】
現在樓上那個(住戶)搬來,她的廚房就給大女兒住,廚房就搬去露台,切菜就在我頭上切 。 有時(清晨)四點半仍然發出嘈音,有次我生氣了,拿支叉向上插(天花板),(樓上)馬上停了(嘈音),她告訴別人我插天花板,四點半他係在發出嘈音,你說多令人討厭。有天我不舒服,她女兒在上面就鋪了大階磚,她的女兒穿著高跟鞋走來走去,很討厭,我都聽到走去哪裡,後來我上去問她媽媽在不在,她說外出了不在,我說你穿高跟鞋外出才穿,你走來走去我都聽到了,隔壁的那個就經常哭,現在我就慘,隔壁那個一天哭幾次,嘈醒我了,唉真是的。

雖然四十多年來,華富邨的人和事都有不同的轉變,但謝婆婆坦言,早已習慣了在這裡的生活節奏,現在最著緊的是,每日可以到樓下的公園和一班老友記談天。
【謝婆婆/ 華富邨住戶】
我現在老了,八十多歲了,就出來坐坐,各有各一座樓,有些在上面,有些在那邊,不過來這裡坐,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便認識了。早上八時半我出來,就坐到十點左右回家,然後睡一會兒,三點半出來坐到六點鐘就回家煮飯。煮飯食便看電視,一邊吃一邊看,吃完碗都不洗了,等到明早洗睡覺。睡在床上又不記得關電視。
根據2011年政府的人口普查,華富一邨超過65歲的住戶,大約有3200人,接近每四個人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家;而二邨超過65歲的,就有2600人。謝婆婆和毛伯伯都認為,華富邨是老人村。政府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,曾經計劃重建華富邨,但係他們都希望不用搬走,可以在華富邨安享晚年。
【謝婆婆/ 華富邨住戶】
我都不希望華富村搬,不希望搬呀,華富村搬了的話,我都不知怎麼辦。一會兒你又搬去那邊,我又搬去那邊,又要另外認識一班新朋友,但是新朋友未必一定夾得到。而且我們都…老實說吧,都不知有沒有命搬,真的,說說又一年,說說又一年,十年八年,我豈會有九十幾、一百歲呀,我現在都八十幾了。
華富重建計劃何時啟動,房屋署指暫時未有實質的時間表,由於計劃還在評估階段,要有整體計劃後才能正式諮詢區內市民,預計要超過20年才能啟動重建計劃。南區區議員歐立成就表示,對於重建,居民都持不同的意見。
【歐立成/南區區議員】
有兩個極端的看法,在華富邨居住超過二十年的原居民,他們絕大部份都不想搬走,他們情願在這個環境百年歸老。另外一些 {trim} 就會覺得華富邨很舊,須要重建,但他們有一個錯誤的消息,就是以爲重建後可以搬回來住,但他們不知道原來重建後,搬走了就是搬走了,華富邨重建後的好是沒有他們份的。
政府會在何時重建華富邨,仍是未知之數。但面臨清拆的豈止是華富村的一磚一瓦,還有一班老人家對這個屋邨四十多年的感情。
Related

作者:黃潔儀(175138) 時光荏苒,社會進步飛快,世人紛紛追求新鮮玩意,永無止境地逐隨所謂「潮流」。提到「舊」一詞則被受世人嫌憎,眾人皆覺戀舊之人是墨守成規的失敗者,不求進步,與社會風牛馬不相及。 「戀舊」一詞出自《后漢書·董卓傳》,意指對過去異常懷念。事實上戀舊之人擁有獨有生活態度,不願隨波逐流,無視世人眼光。 舊人舊物自有其可愛之處,用心細看必改你故有定義。 公共屋邨是香港的本土特色,見證着時代的變遷,記錄了港人的情懷,但香港的舊型公共房屋現已所剩無幾。 華富邨是香港最著名的公共屋邨之一,部分樓宇可飽覽海景及鄰近豪宅貝沙灣,有「平民豪宅」之稱。豪宅與屋邨只是一邨之隔,對比強烈,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。 此外,華富邨部分樓宇採用了雙塔式設計,有別於是舊有設計,具有特色。但是,華富邨被列重建計劃名單中,理應好好記下面貌,莫待清拆成追憶。
In "大學校園"

位於油塘與藍田之間的茶果嶺村,存在至今超過400年,亦是香港僅餘的木屋區。英國與大清在1898年簽署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時,茶果嶺未被納入租界,直至1937年,港英政府劃分新九龍,茶果嶺被歸為租借地,村民失去了原居民身份和丁權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,部份湧入香港的難民選擇聚居茶果嶺,興建了大量木屋和鐵皮屋,一頁又一頁的歷史為將來的收地困難埋下伏線。 茶果嶺村內的窄巷僅容得下一人,有些通道更只可側身、緩緩地通過。走了好一段路,便會看見另一個入口,入口當眼處有一間士多,內裏一頭灰髮並戴著一副老花眼鏡的婦人——馬太,就是士多的老闆娘。「我一開始唔係喺到開舖㗎,都唔係住呢邊(士多附近),我住前少少。」馬太指著麗港城附近的木屋說。1984年茶果嶺火災,原來的家付之一炬,馬太無可奈何向親戚借錢,方成功搬到位於順利邨的現址,剩下的錢就在村口位置開了這間士多。「呢到都養得起三個仔,算係咁啦。」各自組織了家庭的兒子,讓六十多歲的她,安心維持於半退休狀態,閒時才由順利邨回到這裡開舖「過日晨」。 遊走於茶果嶺迂迴曲折的道路期間,不時會與操「大陸口音」的人擦身而過。「茶果嶺不是只有香港人嗎?為何有這些人住在此地?」「佢哋係上面(中國大陸)落嚟,住呢度搏收地,上公屋。」 走前兩個街口,茶室門前坐着位一位個子矮小的老人,他是華叔,在茶果嶺住了五十多年。「以前好多人㗎,夜晚都會有人行嚟行去,成日都瞓唔著。」華叔對訪問見慣不怪,說到「興起」,行動不便的他仍然堅持去拿出茶室以往的報導,向記者娓娓道來。「我老竇嗰代已經喺到搞茶室,咩都有得賣,雲吞麵、嘢飲、雪糕呀......全香港得翻幾間(茶室)有茶室牌,其中一間喺中環。」華叔已過退休年齡,但未言退,問到政府有否向居民提及收地,華叔笑指沒有:「由我細個講到而家,話收咗幾十年都冇聲氣。」 幾十年來,一直有消息指茶果嶺會進行收地重建,惟政府一直未付諸實行:在主權移交前,港府曾打算收地,重建茶果嶺村,卻因地契複雜而放棄;2019年,政府在施政報告提出有意將茶果嶺一帶重建,以應付港人的住屋需求,唯去年當茶果嶺鄉民聯誼會,連同私人發展商萬彩國際,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興建5幢公營房屋和2幢私人住宅,同時保留4幢歷史建築,遭到規劃署的反對。 收地重建一事,在茶果嶺彷佛只是「雷聲大,雨點小」。重建工作談論了幾十年,從未有實際行動。木屋區內生活環境惡劣,電線在頭頂上交織,如發生意外,後果實在不堪設想,但是居民想離開,只能靠自己努力「向上流」,為何其他木屋區(如鑽石山),可以清拆重建,但茶果嶺就要被遺忘? 政府經常宣稱香港地少人多,實質上,不少土地都具有發展潛力(如茶果嶺村,新界棕地等),但往往因處理麻煩而擱置計劃,而取而代之的方法,是以自然環境「埋單」(如「明日大嶼」和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」)。作為面向國際的都市,發展固然重要,但在發展之前,似乎亦需要對本地居民的利益和自然環境的保護作出更多考量。 攝影及採訪:邱景煜 圖片編輯:邱景煜/黃玲燕 編輯:黃玲燕
In "新聞攝影DEBUT"

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自2007年3月正式展開,當中牽涉的業權逾1653個,包括物華街臨時小販市場及協和街小販市場經營的商戶。2019年,所有接受市建局搬遷方案的商戶均需離開,在裕民坊最後留守的一間果汁店亦在2021年遷出,當時未肯在限期前搬離的商戶被市建局人員強行抬走清場。 裕民坊有多達130個舊商戶搬到凱滙基座商場裕民市集內經營,大部分人都上了年紀,決心繼續經營。經一條電梯直落裕民市集,舖位透過地下街的形式做生意,盛載觀塘數十年來的回憶。83歲的海記文具店檔主「海叔」認為裕民坊重建,要搬到市集擺賣對生意額有一定影響。他說未重建之前,自己專營舊大廈住戶的生意,如今大部分舊建築已被清拆,生意額隨之減少,「以前做到開巷食飯都唔得閒,依家好悠遊。」他又指出,有些檔主甚至接近零生意,但因為上了年紀沒有辦法,唯有繼續做下去。另外,「海叔」表示以前擺檔的位置雖然環境較惡劣,但勝在生意好,「街坊朝早買餸又經過我,夜晚買完餸又經過我,真係唔休做。」 「海叔」與文具檔 「海叔」自1974年開始在瑞和街街市擺檔,13年後街市拆卸,「海叔」曾被安置到物華街臨時小販市場,多年來與舊街坊建立了深厚感情,「舊客搵返你好開心,買唔買嘢唔係問題,好有感情,依家唔係賺錢。」對於觀塘市區重建的看法,他表示市區擁有新容貌是好事,但觀塘仍然有很多舊樓,擔心樓宇安全存在隱患。 被問到市建局當年除了向被逼遷商戶作出賠償外,有否提供其他支援,「海叔」指自己與市建局高層人員的關係如同朋友,「好多大茶飯嚟搵我傾偈。」他說對方會定期詢問其意見和需求,但職員「講就接受,做嘢照舊。」他指所有事情都要自己爭取,例如檔位原本燈光不足,向市建局提出的要求亦無回音,「講咗年幾先有燈」。他自言一向積極表達意見,又認為有些舊商戶想說出口但是根本沒機會或是不敢開口。 牛嫂與以賣帽為主的城記舖位 在海記文具店隔離檔口的城記,曾在物華街擺檔53年,昔日為玩具店。78歲檔主「牛嫂」指市集舖位細,現時已賣不到玩具,「嗰時好好生意,有賣帽,玩具,雨褸乜都有。」她表示,疫情下人流比以往差了很多,加上現代小孩都接觸電子產品,無人再買「老土」玩具。 城記玩具店悉日在物華街的檔口 「牛嫂」表示,市建局當年只賠償很少金錢讓舊商戶搬遷到市集營運,之後並沒有提供相關援助,「應該俾多少少錢,唔係我哋點生存到。個牌係個女,但我幾廿歲人離唔開個檔,同街坊好開心有傾有講。」她又表示,重建後的觀塘區,環境得到很大改善,拆卸重建始終屬好事。 採訪、攝影:吳欣宜
In "大城今天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