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:奪命書生
觀塘裕民坊在市建局的重建方案推展下,終於迎來撤離的日子。一眾老街坊、舊商戶,只能各散東西,追憶昔日情懷。就在2月24日,筆者參加了「告別裕民坊展」,希望藉此重燃一下自己對觀塘區的熱情;也許,以「(地緣的)情」養「(批判的)思」才是最終的得著。

一位店主分享道:「這裏(觀塘)是我的根。」以根為喻,沒有甚麼出奇之處,落葉歸根、草根階層等等用語,比比皆是。有趣的是,店主並沒有把觀塘當成「泥土」,即「提供物理存在及供應生長的必要條件」。若說觀塘是「根」,哪麼店主在這比喻中,是一個怎樣的存在?他是如何理解自己與觀塘的關係呢?根,是植物的構成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器官。「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。」說明了即使小草沒有了葉片,放眼一片焦土,只要泥土下的草根,沒有被連根燒毀,小草就有重生的可能。如是說,店主(主體)將觀塘(地域)視為「我」的有機整體,他自己必然是這個植物式整體的一個器官,並由該生物的最初生長的部分,即「根」的發展下,成為了互相支援、構成的存在;他可能是「葉」、「花」、「果」或「莖」等等,但可能確定,如沒有店主的部分,這個生物是沒有辦法成立。因為,店主作為「我」,將自身的存在及構成歷程,與觀塘這無機物的發展相互連結,形成一種結合人、地域及歷史的「主體性投射」。同時,這也是「空間的重疊及創生」——透過人的思維中的概念性空間,突破至真實的物理性空間,兩者結合成一種缺一不可的存在。因此,在理解一個地域、社區時,當地人的文化、政治、經濟等等發展,也是通往認識的鑰匙的一部分;唯獨如此,他人眼中的地方才能「活」起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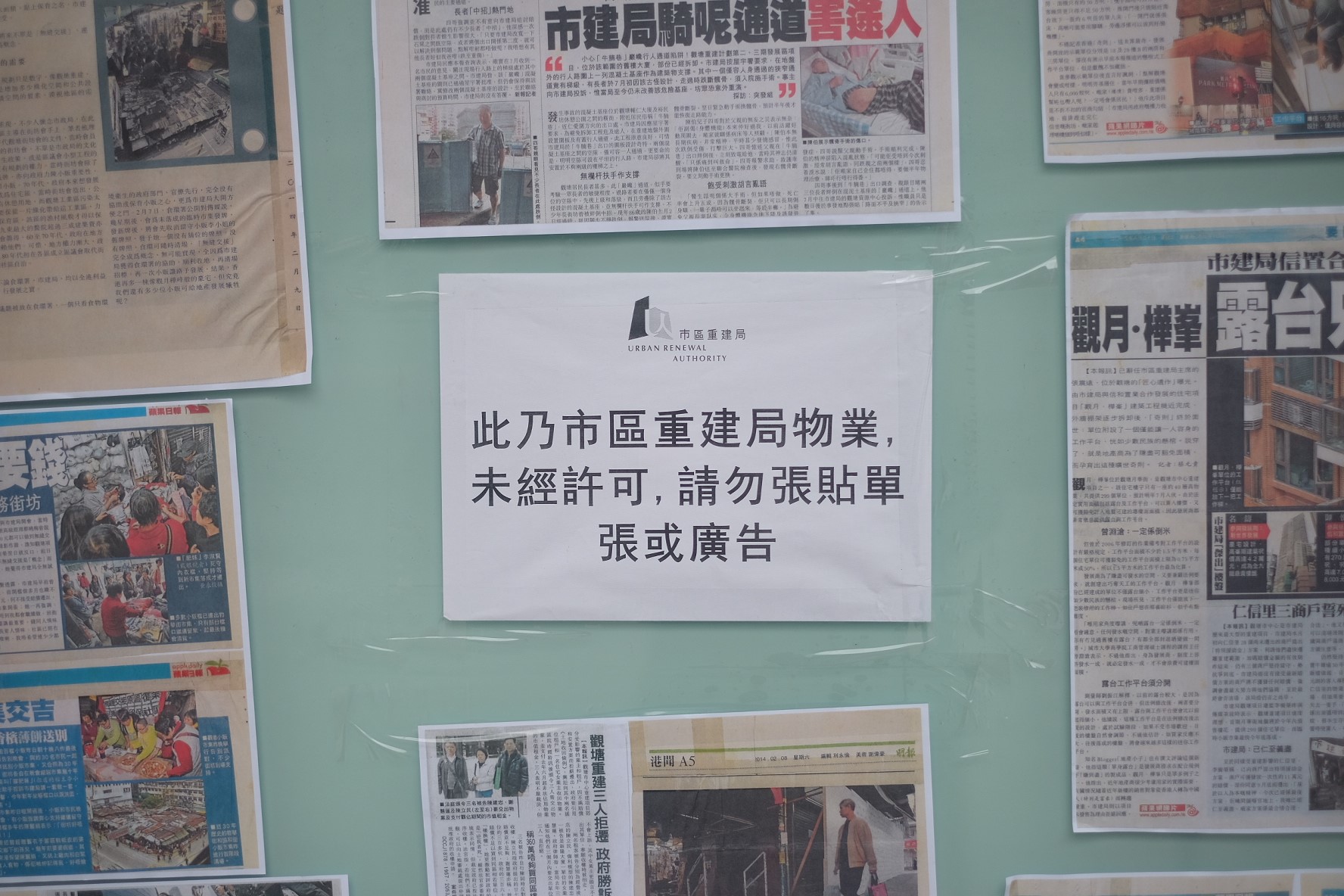
按照以上所說,「活」的前提是人要投放自己過往的地緣歷史至地方上。哪麼,把以往的風土人情、傳統,通通從倉庫底發掘出來,加以利用,不就「活」嗎?近來,筆者觀察到香港的各大商場,開始引入以「冰室」為主題的(偽)舊式餐廳。這是要把商場「搞活」嗎?非也。大商家只是在借屍還魂,說得難聽點,他們是用錢鞭冰室的屍,那怕它在商場以外的地方還未死!傳統(或草根)文化的召喚,正在香港漫延開來。不同人將傳統應用在不同的情況,如上述的「告別裕民坊展」;政府剛提出美食車時,有團體以小販車仔提倡另類方案;以及本土派團體吸納支持本土本位意識的選民的選票,開始(並結束短暫的)立法會議員的生涯。傳統文化在不同層面的涉入,的確引發「活」的苗頭。但有一點值得關注,除了懷舊外,我們應如何擁抱未來?正如中國的詩,有古體詩和近體詩之分,難到發揚自唐代的近體詩不「古」嗎?在現代的人看來,古。為何當時的人要定下古近之別呢?無非要弄個涇渭分明,定好位,容易歸邊。若沒有古,卻也沒有近,兩者之間的相對性確立對方及自身的存在。所以,以傳統之名行事之人,是對抗「現在」?他們對抗的,應是傳統以外的「非傳統」。傳統是以往指定的政治及文化下存在的人的生活方式。至今,這群人仍沒有消亡。不過,政治及文化卻已急劇改變。重新把人的傳統的概念性空間,勾勒在現實中,所產生的作用,就是統合認同這空間的人,從而挑戰非傳統的架構。這份由傳統提供的能量,轉化成與非傳統的角力,亦是提倡傳統的人樂見的結果。

角力過後,會是甚麼?由傳統而生的角力,彷彿沒有提供任何方向,就如一頭追住自己尾巴咬的小狗,雖是「活」起來,卻一直原地自轉。有人說,香港要獨立,香港要排除非香港的人或事物。若然如此,傳統豈不是又一次被鞭屍?當我們提倡傳統時,只留意到它的獨特形式,如裝橫、質感等。傳統的品質是甚麼呢?這份品質,與當下的環境,應如何結合,加以理解呢?那品質是獅子山精神嗎?不得而知。可以確定的是,舊的傳統所忽視的新的傳統,正在形成。新的傳統,是舊的傳統在新時代下的產物,而不應被看待為非傳統。沒有人能徹底重現過往的場境,並將傳統復甦,這樣只會令它成為異物,時間久了,它將難以自存並失效。但是,新的傳統面臨一大難題,就是它的年代不夠久遠,了解它、認同它的人仍然不足;可以說,人們對它的認知尚未建構。這一過程,可是深耕細作,可幸的是,它會活上好一陣子。另外,當中互相構成新的傳統的人,比起舊的傳統中的人,更有時代的觸覺,更有條件過渡至不確定的未來。希望他們能利用新時代的科技應許的一小部分自由(尤其是網絡空間、網絡社群),進化成一種「自為根」的存在,更有效的抵抗時代巨輪的滾動。

新的傳統,需要新的發掘。若只寄望因政策或經濟活動而即將離開的人,藉著他的舊的傳統,呼喚他人的認同,無疑只是吸引眼球,目睹這個行將就木的「活」物的生命的結束。那次最後的懷舊,不過是預先舉辦的喪禮罷了。活在這兒、那裏,還是留給有生命力及可能的新的傳統吧!讓我們早點懷新,以免還未珍惜它的「活」,就要哀悼它的「死」。





